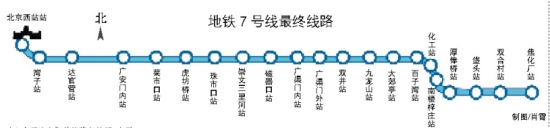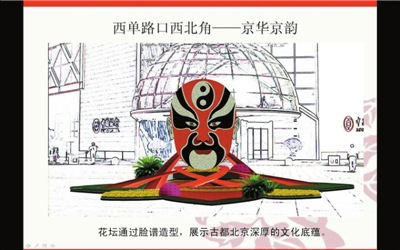展江认为,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使中国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面临的权益问题浮出了水面。
一位资深记者认为,这一切其实都可以归咎于公权力和媒体间的博弈。他认为,如果博弈的结果,导致记者连最基本的采访权都被剥夺了,那将是最悲哀的事情。
“采访权在新闻学科里,并没有专门解释。法律里可能把它归纳到知晓权里头。采访权,严格说也不是记者的特权。记者不过是代替了公民或者代表了公民,行使了知晓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介绍说。
违法成本低导致“记者劫”升级
法治周末记者 莫静清 法治周末实习生 张玮鸥
记者在伊春被扣之后的结局是,两个小时后重获自由,伊春市宣传部门和警方就此事公开道歉。
王南回忆说,一个警察过来用命令的语气对他和王舜天说:“领导发话了,你们可以走了,但不能再去殡仪馆了!”
3个小时后,伊春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华景伟说,这是“误会”。
随后,伊春市公安局伊春分局崔姓副局长向在场十余家媒体记者道歉:“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在这次事件中受委屈的记者表示歉意。”
最强硬的介入,最柔软的道歉,这几乎是所有“记者劫”事件的结局。
专家指出,这其中固然有媒体记者不想再“惹麻烦”的原因,但更多是公权力强权的表现,而这或许是“记者劫”事件不断升级的原因。
官方一句道歉了之
不同的事态同样的结局
7月29日,仇子明事件,最后以遂昌县公安局撤销刑事拘留决定、赔礼道歉而收场。
8月6日下午两点多,在吉林省桦甸市常山镇派出所情报室里被扣押半小时后,记者王立三和朝格图重获自由。
之后据某记者微博(http://t.sina.com.cn)透露,常山镇派出所和桦甸市宣传部官员对记者道歉。
在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建顺看来,仅以一句道歉来了结“记者劫”,与这样的行为本身造成的不良后果并不相称。
“对记者的伤害,不是对记者个人,而是对记者所代表的媒体,和媒体身后的广大公众。”杨建顺认为,这种行为是公权力对媒体的直接挑战,“特别是记者在吉林省采访洪涝灾害被扣的事件,不是‘误会’问题,而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是向宪法保障的媒体监督之权利的宣战。”
他不无担忧地叹道:“‘无冕之王’都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更何况普通公民?”
从实践来看,记者在权益遭到侵犯之后,官方多以“道歉”终局。更严厉一点的,也仅仅是对整个事件中的相关民警或者保安进行处罚。
2010年3月23日,《京华时报》两名女记者采访一起火灾时,被院内多名男子强行架出现场,对方称为“保护记者安全”。后来,物业公司的上级管理机构以开除当事安保人员了事。
更早之前,发生在广州市罗湖文华花园采访现场,《南方都市报》记者遭两名警察辱骂、威胁、推搡和殴打的事件,也仅是对当事民警作出暂时停职处理。
对此类事件发生后,记者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杨建顺和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魏永征都表现出某种无奈。
魏永征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记者正当的采访权利不能满足时,确实没有什么有效的救济措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规定了政府有公开信息的义务,也规定了瞒报、谎报的法律责任,但那是对上的,记者不能以此直接寻求救济。
记者很少诉诸法律
“无冕之王”维权艰难
从记者一方来说,也很少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多是为了避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曾经有记者试图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5年发生在上海的全国首起新闻记者采访遭拒案,被视为司法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当时,上海市立法规定政府信息公开之后,《解放日报》记者马骋据此多次向上海城市规划局索求城铁规划的相关信息,遭到拒绝。
2006年5月18日,马骋将上海市规划局告上了法庭。之后,承受了巨大压力,被调离采访岗位。
2006年6月7日,马骋提出撤诉申请,理由是:申请人放弃对被申请人的采访申请。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同年6月26日,马骋第二次起诉上海市规划局。与两年前的信息不公开不同,这次他的起诉理由是:公开的信息之间互相矛盾,规划局涉嫌行政违法。结果,法院没有受理案件。
与马骋的选择不同,更多的当事记者没有诉诸法律。
在一名资深媒体人士看来,媒体记者之所以不诉诸法律,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一来与我国媒体的现状有关,受限颇多,考虑自然也多;二来与司法救济道路难走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公权力对媒体的违法成本偏低,主要是相对于新闻监督机构和公众来说,公权力具有强势地位。加上对公权力机构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导致公权力一般不害怕犯错误。
“目前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公权力机构来说,约束力不是很大,因此难免出现某种执法惯性的形成和‘潜规则’的盛行。”莫纪宏一语道破。
当媒体遭遇地方公权力
法治周末记者 温泉 法治周末实习生 张玮鸥
短短11天的时间里,见诸于报端的公权力机关与记者之间的冲突就发生了5起。
半个多月后,今年8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
温总理话音未落,8月28日,伊春空难发生4天后,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就接连发生了4名记者遭警方扣留事件。
公权力与媒体间的博弈由此可见一斑。在专家看来,两者间的博弈,既是官本位思想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反映,是各种不良利益集团拉拢腐蚀、威胁打压媒体的表现,也是媒体地位低微的表征。
由“蜜月”到“冲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在2008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角色认知的变迁》中总结说,改革开放之前,传媒的职能被定义为单一的政治宣传,记者是党的宣传工作者,而不是一种社会职业。
上世纪80年代从事实务新闻工作的人,在他们关于自身工作的文章或书中,也是在强调记者角色的政治性质。
在此期间,由于媒体的特殊职能和地位,媒体与公权力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记者职业角色开始有所转变。媒体与公权力由“蜜月”渐渐转向“冲突”,记者也从此时开始维权。
1998年8月18日,中国记协成立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委员会就是一个标志。
2003年,媒体与公权力共同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有地方瞒报、谎报信息造成“非典”疫情蔓延,后来不得不公开信息形成社会合力化解危机。
这一年,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失语。全国整顿行业报,数百家新闻性不强的行业报和县级党报停刊,引起了学界对“新闻专业主义”较为集中的研究。
“新闻专业主义基于以新闻报道和传播本位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倡导着新闻记者践行一系列职业规范。”陈力丹说。
对日益市场化的媒体而言,满足公众知情权显然成了当务之急。
“真正的新闻记者,会一直对政府保持高度的‘雷达’状态,这是媒体的基本属性。”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认为,“媒体的基本功能是告知、监督、启迪,记者的职业,是采访新闻信息,尽可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公权力的有力监督。因为公权力最容易伤害公民权利。”
王克勤说:“媒体的属性是公开和传播。一个要曝光公开传播、一个是隐蔽和遮挡,无论什么样性质的问题,只要不愿意被公开、不愿意被曝光,那它天然地和媒体之间就是抵触的,或者是不欢迎媒体的。”
竭力“控负”挑战媒体
媒体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大众传媒在我国迅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2000年以后,伴随网络媒体的逐渐强大,“网络反腐”获官方认可。
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条。
现在,网民人数已近4亿的中国,官员的不当言行因被网络曝光而被处罚甚至入狱的事情并不鲜见。
信息传播路径的多元化,使得某些地方公权力对媒体的控制更加困难。“但紧接着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些人力图阻止记者获取信源。”王克勤苦笑着摇头。
根据多年的采访经验,王克勤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每每发生突发事件,地方立刻会成立一个强大的突发事件应急小组。“把事件的关键当事人、目击者或控制或遣散,记者到现场,一个人都找不到。新闻的力量在于事实与真相,干脆让你无法接近核心信源,你就没有力量,就形成不了任何威慑”。
“而记者就成了当地公权力的‘心腹大患’。”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无论是灾害、事故还是腐败,他们都不愿意让记者采访,认为应该‘控负’(控制负面新闻)。”
“当然,还有维稳思维。他们认为,控制不了的记者是破坏稳定的根源之一。”展江说。
展江认为,中国记者所遭遇的职业困境,主要表现为各种不良政商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拉拢腐蚀和威胁打压,而且愈演愈烈,花样翻新。
“中国新闻采访报道正进一步深化甚至出现某些转型,当企业的产品关乎公共利益、上市企业牵涉到公民利益时,媒体的报道内容亦开始涉及企业利益,而企业利益又和地方政府利益挂钩。”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教授认为。
即便如此,某些地方公权力为什么敢公然挑战媒体?
多数声音认为,违法成本低,是这些地方公权力“乐此不疲”与媒体博弈的原因,也是导致“记者劫”一再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